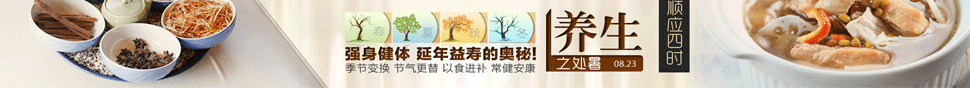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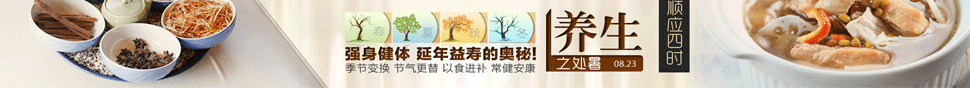
我初读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时便听说过毛姆“二流小说家”的名号,那时的我对于这样的名头还不大能接受,纵使后来知道所谓的“一流小说家”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,也还是会有些奇妙的感觉。《随性而至》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个月才读完,看到其中率性而又坦然(并不确切,我相信所有写作者都不可能真的“随性而至”)的毛姆,才确信“二流小说家”是一个自由又可爱的称呼。
我实在无法形容我有多喜欢毛姆,即使他的文章因着同性恋身份或多或少显得有些厌女。我总觉得毛姆是一个浪漫到极致的人,他天生就该做小说家。应该怎样去形容浪漫呢?我以为它是一种毫不掩饰的纯粹的渴望。毛姆一贯站在客观理性的局外人立场,但我确信这其中掺杂了太多对于美的欲望,这种欲望使得毛姆可以抛弃道德伦理的束缚,安心地去看待人性当中赤裸裸、不加掩饰的罪恶面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他一贯维持的旁观者形象,也是一个浪漫的想法,而我喜欢他的浪漫。
《随性而至》的可读性很强,正如他一贯倡导的那样。老实说这是我喜欢毛姆的最大原因,在探索语言的更多可能性之外,不能忘却的是身为写作者的基础职能——传递。这一本文艺评论集也可以算作是一本八卦杂志吧,毛姆在其中表达了一些他的喜恶。于我而言,《苏巴郎》这一章有非常强的感染力,我在下面摘抄两段:
他那剃过的头颅上仅剩的一点头发似乎是红褐色的,由于长期斋戒而过于消瘦的脸庞上有一种不安、热切的张力。他的面颊蒙着一层激动的红晕。他的皮肤比象牙色暗,但带着橄榄色的那种病态的细腻。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打结的绳子,一只已经残废的手紧贴在胸前,另一只手中攥着一颗滴血的心。
艺术家不需要背着沉重的行囊才能找到流传后世的路。几幅画,一两本书就足够了。艺术家的功能是创造美——尽管这在我看来并非他创作的直接动机——而非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揭示真理。不然的话,三段论就比十四行诗更重要了。毛姆《随性而至》苏巴郎应该是一个老实、古板的人,但在毛姆的叙述中他被赋予了一种神性,一种强烈的浪漫气质(原谅我用了这么多次的强烈,我实在是找不出更合适的形容词了)。这章中有大量的篇幅在讨论美是什么,希望在未来重读它的时候我会对这些描述有更深的见解。那么,便不多言了吧。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